亡國戰火下的官僚騷操作:鴉片戰爭失敗的局部細節
暗歷史:大歷史深處的瘋狂與幽暗人性
1840 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變局。
未開戰之前,處於「天朝上國」迷夢的清政府,覺得地大物博,擁有四億億民衆,優勢完全在我。
交戰後,清政府才赫然發現武器、軍隊、後勤保障等,與敵人相比,處於全面下風。
廣州三元里抗英的勝利,一度讓清政府認爲民心與精神的力量可以令其反敗爲勝。
可官僚系統的腐敗與落後,嚴重地破壞了軍隊的戰鬥力。
在這場關乎國運與民族存亡的戰爭之中,小官員趁機大發國難財,皇親國戚則醉生夢死、貪污索賄。
今天要講的故事發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期,在大小官員花樣百出的騷操作之下,畢其功於一役的反攻行動,僅 4 個小時就被英軍瓦解……
亡國危機
1841 年 10 月 18 日,一份前線快報遞到道光皇帝的面前。
儘管已經有心理準備,但消息的糟糕程度還是道光皇帝的出乎意料:鎮海失守、裕謙殉難。
自鴉片戰爭爆發以來,屈辱與慘烈的失敗,接踵而來。
短短的一年中,戰敗的消息就像英國的炮聲一樣,密集轟炸着朝野內外。
1841 年 2 月,虎門淪陷,固若金湯的靖遠、鎮遠、威遠,鞏固等炮臺,慘遭英國炮火的降維打擊。
六十二歲的老將關天培戰死。英軍佔據獵得、二沙尾,廣州自此門戶大開。
1841 年 10 月 1 日,定海再次失守。
定海的五千守軍,在軍糧匱乏的情況之下,頑強抵抗六日六夜,慘烈失敗。
攻下定海後,英軍於 10 月 10 日早晨,沿着大峽江進軍,兵分東西兩路,從金雞山區域和招寶山、鎮海縣城發起猛烈的進攻。
鎮海戰爭開始時,欽差大臣裕謙信心滿滿。
炮火威力的差距,加上浙江總督餘步雲棄城逃跑,轉瞬之間,鎮海就被英軍攻陷。
裕謙絕望之下,跳河自盡,後被家丁救起,次日走到餘姚時氣絕身亡。
鎮海的淪陷,讓在「戰」和「撫」之間遊離的道光皇帝,終於「是可忍孰不可忍」,即刻從江蘇、安徽、江西、河南、河北等八省調兵 1.2 萬,重整大軍,準備反攻。
接受反攻重任的人,乃是楊威將軍奕經。
愛新覺羅·奕經,生於 1791 年,至 1841 年,已年滿五十。在官場之中,他早就混成經驗嫺熟的老油條了。
奕經當過帶刀侍衛,也隨軍出征過。不過,他在履歷之中,文職居多。
對於軍事、軍務,並不擅長。
但他有個與生俱來的長處——血統純正的皇室宗親。
奕經是雍正乾隆皇帝的四世孫,道光皇帝的侄子。
10 月 30 日,奕經離京南下,11 月 23 日到達江蘇揚州,離主戰場浙江咫尺之遙。
此時, 一位聲稱能鑑別漢奸的男人,出現在奕經的眼前——鴉片戰爭中,由漢奸組成的帶路黨,讓清政府喫盡了苦頭。
男人名叫鄂雲。
一名默默無聞、窮困潦倒的直隸州候選知州,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開始了一系列的騷操作,薅起了清政府的羊毛,差點實現升官發財的美夢。
鄂雲其人
鄂雲原名叫聯壁,出身、年齡不祥,在刑部當過司官。
清朝的司官,品級在正五品以下、正六品以上,地位較爲低下,是具體做事的技術官僚。
鄂雲的仕途並不順利,很快就被革職。
革職的原因是什麼?已不爲人知。
想必是犯了錯誤,或得罪了某些權貴。以至於鄂雲覺得在京城沒有出路,只能鋌而走險,私逃出京。
鄂雲先在南京落腳。
1837 年,鄂雲從南京搬到杭州,到處打點、運作,通過捐納得到直隸州候選知州的資格。
候選,就是備胎。
看起來鄂雲即將成爲朝廷命官,其實是遭遇官場中的「PDD 騙局」——你已經解鎖了 99.99% 官員資格,再「捐一刀」就能成爲知州大人哦。
清朝中後期,隨着財政的惡化,各地遍設捐局,只要給足了銀子,就給個候選官員的身份。
賣官鬻爵蔚然成風,捐官內捲成紅海。
朝廷的編制只有那麼一點點,因此十幾人、幾十人補一缺。
因爲十年甚至數十年不得補缺的現象,比比皆是。
清政府只要銀子,不要身子。
鄂雲捐官、買官已花完全部家產,陷入了貧困境地。
若是沒有戰爭,鄂雲也許餘生都沒有翻本的機會。
因此,英國人的入侵,在別人眼中是危機,在鄂雲眼中卻是千載難逢的機遇。
從 1841 年初開始,鄂雲就四處奔波,尋找「報效祖國」的機會。
鄂雲先到鎮海投奔欽差大臣裕謙。
一見到裕謙,鄂雲就表情浮誇、演技做作地背誦了大清封建社會價值觀,痛罵英國鬼佬之餘,淚流滿面。
裕謙聽了非常感動,然後拒絕了鄂雲。
理由是,鄂云爲人輕浮,辦事不牢。
裕謙像是打發叫花子一樣,給了鄂雲幾兩碎銀。
鄂雲只得灰頭土臉地離開。
鄂雲沒有灰心,前往巡撫劉韻珂的官署,表演了一番精忠報國的戲碼,希望得到任用。
劉韻珂出身拔貢,做過刑部的七品小官員,和鄂雲做過同事。
劉韻珂也曾是苦逼的候補,連續七年未曾獲得錄用。
鄂雲的痛苦與焦慮,按說劉韻珂是深有同感。
然而,劉韻珂深知鄂雲的爲人,知道他辦事不牢,只是給了他 30 兩盤纏,算是救濟一下窮困潦倒的舊同事。
此後,鄂雲沉默了一段時間,等待新機會。
果然,年底時,他在堂弟聯芳口中得知,楊威將軍奕經到達揚州,準備驅趕英國人,收復失地。
聯芳,是奕經的隨員,官職爲步軍統領署七品筆貼式。
筆貼式,是清朝的官名,意爲辦理文件、文書的人,主要工作是翻譯滿漢章奏文字、記錄檔案文書等事宜。
換言之,聯芳雖然品級低,但話語權與影響力並不小。
經聯芳的引薦,鄂雲順利地見到欽差大臣奕經。
鄂雲吸取前兩次的經驗,沒有做作的表演,而是故作神祕地跟奕經說:「大人,我有辦法辨別漢奸。」
在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的堅船利炮固然厲害,但尤讓清政府恨得咬牙切齒的是說着「Sir,this way」的漢奸。
漢奸們不像洋鬼子那樣,黃髮碧眼,說着鳥語,讓人一望便知。
他們腦中沒啥忠君愛國的思想,只要錢給夠,就敢給洋人帶路。
奕經一聽,立馬精神起來,問:「先生有啥妙計?」
鄂雲眉飛色舞地說:「背誦!拿《論語》一冊,隨機抽查。背誦時,支支吾吾,口語不清,或面露痛苦之色,定然是漢奸。這批人,無君無父,在孔聖人的教誨之下,必會原形畢露。」
奕經一拍大腿,讚道:「先生高見,實乃臥龍鳳雛再世。」
鄂雲獲得奕經的信任,得到一份招募鄉勇的肥差。
望眼欲穿的機會,流着油水的肉,就這樣掉在鄂雲的嘴裏。
鄂雲拿着奕經的任命信,多次往來江蘇與浙江之間。
鄂雲再次與巡撫劉韻珂、御史呂賢基見面時,散發出 「昨天你對我愛理不理,今天我讓你高攀不起」的氣場來。
鄂雲對劉韻珂說:「我和欽差大人談笑風生,我弟弟是欽差大人身邊紅人。」
鄂雲對呂賢基說:「我和欽差大人是異父異母的親兄弟。」
鄂雲徹底飄了。
作爲官場的老油條,劉韻珂、呂賢基知道鄂雲算是奕經的人,暫時不能得罪。
看着鄂雲洋洋得意,兩人露出「我就靜靜看你裝逼」的微妙表情來。
等鄂雲離開後,兩人轉頭就交待下屬,對鄂雲要多加提防。
國難財的機密
1841 年年底至 1842 年年初,浙江各級官員處於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狀態中。
清政府與英國的交涉處處被動,大戰一觸即發。
形勢危急如此,鄂雲的內心自然是心急如焚。
但他的心急,並不是戰場上的成敗,也不是國運的衰敗,而是如何最有效率地斂財,最大程度地爲自己謀取私利。
1842 年 1 月 9 日,是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離新年還有一個多月。
與往年口袋裏窮得叮噹響相比,鄂雲懷揣着一筆鉅款,可以過個好年。
此前,鄂雲拿着奕經的條子,以招募 500 名鄉勇的名義,在浙江糧臺提取了將近 5000 兩銀子。
鎮海失守後,慈谿縣後山泊地區人心惶惶,生怕英國人打過來。
鄉紳們紛紛招募鄉勇,保衛家鄉。
鄂雲馬不停蹄地來到慈谿縣後山泊。
見到鄉紳們,鄂雲大肆宣揚着「我和欽差大人奕經的交情,勝過親兄弟」,並宣稱調赴曹江,正爲朝廷辦事。
鄂雲鄉紳們沒見過大世面,紛紛相信了鄂雲。
於是,在鄉紳們協助下,鄂雲招募了大約 500 名鄉勇,給每人發了 1500 文錢。
這是定錢、盤費、器械等的費用。
由於前方緊缺人手,1842 年 2 月 8 日,鄂雲帶領着這批鄉勇趕往紹興曹娥。
到了紹興,鄂雲的騷操作又來了。他帶着奕經的條子,來到紹興糧臺,以續僱 113 名鄉勇的名義,提取了 4500 兩左右的銀子
也就是說,以僱傭鄉勇的名義,鄂雲向清政府要了兩次錢。
雙贏!
糧臺官員們看不出其中的貓膩嗎?
不可能。
即使知道其中的貓膩,官員們還是要給錢,畢竟鄂雲手中有欽差大人奕經的條子。
雙贏還不算,鄂雲還有更騷的操作。
從曹娥前往鎮海時,鄂雲僅給每人 800 文錢,折算下來,只有半兩銀子。
中間商的血管裏,每一滴血都帶着銅臭。
這一趟差事下來,鄂雲至少淨賺 5600 多兩銀子。要知道清朝農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十餘兩銀子。
不費吹灰之力,鄂雲就擺脫了赤貧,實現了財富自由。
而那些冒着生命危險上戰場的鄉勇們,在鄂雲手中拿到的銀子,還不到 2 兩。
如果考慮到清朝各衙門喫空餉的傳統,鄂雲招募的鄉勇,未必有 500 名。
其中操作的空間有多大,想想就刺激。
換言之,鄂雲賺到的錢,遠不止 5600 兩。
然而,鄂雲的騷操作遠不止如此!還有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操作。
那就是宣稱捐了 12000 千文錢,按照 1000 文等於 1 兩銀子計算,鄂雲捐獻了 12000 兩銀子。
根據《海疆捐輸議敘章程》的規定,候選直隸州知州捐獻 8000 兩,可優先補缺。每多捐 500 兩,則加一級。
那麼,這 12000 兩銀子,是實繳嗎?
想想也不可能。
想要鄂雲手裏掏出銀子,比殺了他還難受。
最大的可能,就是鄂雲利用職權給給自己添個捐納的名額。
如果事後朝廷追查捐獻的銀子呢?
鄂雲完全可以說,都用在僱傭鄉勇了。
那鄉勇呢?
鄂雲可以說,打仗時逃的逃、死的死。直接來個死無對證。這筆糊塗賬,朝廷查無可查,最終只能不了了之。
經過一番騷操作,鄂雲不但發了財,還極有可能實現了升官的美夢。
意不意外?驚不驚喜?
奕經的騷操作
更驚喜的還在後面,鄂雲充其量不過是個小角色。
愛新覺羅純血、清高宗四世孫、道光皇帝之侄奕經的騷操作,簡直是「竊國者侯」的完美詮釋。
鴉片戰爭到 1841 年年底,清政府上下的心態都崩得七七八八。
道光皇帝彷彿患上了「精神分裂」,一邊覺得自己是主場作戰,有四萬萬人民,堅持作戰到底,一邊又覺得敵人的堅船利炮太厲害了,註定打不過,想要投降認輸。
可投降的說法,實在太過於刺眼了,道光和大臣們一起發明了「撫」。
自我安慰 buff 加滿。
道光的政策在「戰」與「撫」之間,搖擺不定,大臣也就跟着搖擺,裝着努力的模樣。
奕經接受收復鎮海的聖旨時,大清失敗的局面其實已難以避免。
奕經深知搖擺不定是道光皇帝的性格本色。
出征之前,已被判斬監候的大臣琦善被道光重新起用,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
琦善獲罪的原因在白河口見到英國的堅船利炮後,私下與義律簽訂《穿鼻條約》,割讓香港島,賠償六百萬元。
此一時彼一時也。
這是道光皇帝的動搖的證據。
所以,奕經拖拖拉拉地從北京赴任,走到揚州時,突然就不動了,理由是等大部隊集合。
奕經住進了滄浪亭旁的行館,隨從的部隊則駐紮在吳縣。
揚州是繁華之地,煙花之都,有聞名遐邇的「揚州瘦馬」,有靡靡之音崑曲。
奕經似乎知道註定要失敗,過着糜爛的生活,利用尋歡作樂來逃避現實的壓力。
眠花宿柳、貪污索賄……這只是奕經騷操作套餐的基本款。
套餐 plus 還在後頭呢。
爲了打敗野蠻的英國侵略者,奕經舉辦了首屆作文大賽,一等獎作文將有機會作爲奏捷文,上呈給皇上。
主題是「如何生動地描寫打敗侵略者?」
賬下的秀才、書生們紛紛參加,寫出無數份詞彙優美、文采飛揚的作文。
閱讀着這批作文,奕經彷彿自己已經打了轟轟烈烈的勝仗。
再者,經奕經研究發現,其他戰役之所以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開戰前沒看黃曆。在不宜開戰的日子裏出兵,軍隊的戰鬥力自然會是減半。
於是,奕經對求佛拜神的事,越發上心。農曆十二月十八日晚,奕經忽然做了個美夢。在夢中,英國的洋鬼子跳上大船,落荒而逃。
這個夢,來得如此及時,奕經喜不自禁。
奕經跟隨員一說,參贊文蔚連忙站起來,口中賀喜不已。
原來,文蔚昨晚也做了個洋鬼子落荒而逃的夢。
其他隨員們瞥一眼文蔚,心想,還是你小子會拍馬屁啊。
隨員們不甘落後,趕緊組織了新的作文大賽,題目是:欽差大人的夢,預示着什麼?
作文收上來,奕經一看,人人都說是吉兆。
奕經心情大悅,手中的勝券又多了一張。
上樑不正下樑歪。
奕經如此騷操作,屬下亦有樣學樣,呈現出擺爛、狂歡的末日氣象來。
奕經的 6 名隨行官員,職位不高,不過是郎中、員外郎、御史、主事、筆貼式、中書之類的五、六品官員,紛紛以「小欽差」自居,得意洋洋,以公肥私。
鄂雲的堂弟聯芳就是其中一員。
大帥如此糜爛,軍隊的風紀又怎麼好呢?
隨行的數百名兵卒,儼然成爲兵痞,整日嫖娼酗酒,貪污索賄,鬧得揚州城烏煙瘴氣。
這羣兵卒,每日要喫掉蘇州吳縣 80 多桌飯菜,消耗數百元。
酒菜稍微差點,兵卒就破口大罵,摔碗扔筷。
就連參贊文蔚的僕從也敢直接進入衙門,大肆喧鬧。
軍隊紀律之差,由此可見。
縣令苦不堪言,怨聲四起。
前線危急,浙江巡撫劉韻珂多次差人請奕經,前去浙江,總理軍務。
可即使如此,奕經嘴上說着「下週動身」,可身子卻誠實得很。
道光皇帝也沒有催促奕經前進,而是默許了休整。
1842 年 1 月中下旬,一個令人奕經痛苦的消息,傳到他的耳中:八省的援軍即將抵達浙江。
揚州雖好,但奕經已無理由流連,只得告別了鶯鶯燕燕,於 2 月 10 日前往杭州,佈置軍務。
半個多月後,奕經趕往前線曹娥江一帶。
此時,是 1842 年 2 月 27 日,離他出京打仗已有小半年了。
接下來,奕經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耗時僅 4 個多小時。
4 小時的反攻
爲了旗開得勝,奕經作了充分的準備。他聽說西湖旁的關帝廟很是靈驗,就在大年初一那天前去求籤。
奕經打開籤一看,只見寫道:「不遇虎頭人一喚,全家誰保汝平安」。
字雖然認識,意思卻不明所以。
大戰在即,奕經哪裏去找虎頭人?
奕經憂心忡忡。
三日後,四川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帶着援軍抵達,士兵們都戴着虎頭帽。
無數的虎頭人立在奕經眼前。
驚喜!
驚喜 plus!
手中的勝券,又多了一張。
奕經心情大好,大大地賞賜了阿木穰部隊一番。
其他兄弟營一看,戴頂虎皮帽就能領到賞賜?
於是,紛紛效仿。
一時之間,軍隊裏都是黃虎頭、黑虎頭、白虎頭、飛虎頭,蔚然大觀。
虎虎生威!
這還不夠,有人向奕經建議,扔一塊虎骨到龍潭裏,激起龍虎相鬥,掀起波濤,可干擾英國艦隊。
奕經的滿腦子都是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奕經還費經周折地調來屬虎的段永福爲先鋒主將。
1842 年 3 月 10 日凌晨 3~5 點,正是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時,奕經下達了總攻的命令。
清軍同時寧波、鎮海、定海進攻。
總兵力在 12000 人左右,聲勢浩蕩的襲擊戰,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失敗了。
用時不到 4 個小時。
在寧波、鎮海、定海三大戰場,英軍僅陣亡一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摧毀了清軍。
在曹娥江東關鎮紮營的奕經,聽到前線挫敗的消息,驚慌失措,恨不得立馬逃走。
幕僚臧紆青一看奕經這副慫樣,知道他一走,必然是兵敗如山倒,便竭力勸止。
奕經接受了建議,心猿意馬地堅持了一夜,第二天便往西奔去,狼狽地逃到杭州。
敗仗是奕經的底線嗎?
並不,奕經的底線,我們想象不到。
安全後的奕經,寫了篇 4000 字的小作文,將敗仗粉飾爲大勝仗,報告給道光皇帝。
渴求勝仗的道光皇帝,看了小作文,深受感動,感恩祖先保佑,準備論功行賞。
戰報會說謊,但戰線不會。
奕經的謊言,很快就被識破。
此後,清政府再也無法組織反擊的能力。
清政府不得不選擇了「撫」的策略。
1842 年 8 月 29 日,南京江面,皋華麗號軍艦上,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鑑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畫押。
條約便是《南京條約》,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條約中要求中國割讓香港島、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元、五口通商、協定關稅、廢除公行制度等。
英國代表璞鼎查志得意滿,來年他成爲香港殖民政府的第一任總督。
鄂雲、奕經的下場
戰爭結束了,清朝的亡國危機暫時解除了。
那麼,鄂雲和奕經的下場如何?
首先來看鄂雲。
鄂雲的罪行被御史呂賢基、浙江巡撫劉韻珂揭露,然後被捉拿歸案。他的最終下場,出現在耆英的奏摺裏。
「鄂雲私逃出京,冒領軍糧屬實。雖冒支各款業已措繳,有盈無絀。應仍按律問擬,鄂雲除革職消除旗檔外,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該革員於解部嚴審時,猶復任意抵賴。情殊狡詐,應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鄂雲保住了性命,只是被杖打一百,流放到新疆當苦差。
「猶復任意抵賴」,是說鄂雲沒有坦白從寬,態度不好,罪責加了一等。
耆英在奏摺中還提到,因戶部出現鉅額的虧缺,與鄂雲相關的人員,都要立案調查。
「均著先革職,並將已故的各員之子有無出仕,及現任何官,詳晰查開單具奏。」
相關涉案人員,除革職之外,其他懲罰,尚且不明——至少,爲鄂雲穿針引線的筆貼式聯芳是被革職了。
而擁有純正皇室血統的奕經,所受到的懲罰,只是自罰了三杯「茅臺」 酒——以勞師糜餉、誤國殃民之罪被革職。
僅過了半年,奕經便火線復出。
此後十年,奕經官運亨通,獲得道光、咸豐的重任。
那麼,奕經的「勞師糜餉」有多嚴重呢?
據貝青喬在《咄咄吟》中的記錄,楊威將軍此行,「徵兵一萬一千五百人,募鄉勇二萬二千人,用餉銀一百六十四萬兩」。
平均到每位兵勇的身上,大約 49 兩銀子,扣除行政、兵器、後勤等費用,怎麼算每位兵勇的餉銀都應該有 10 兩銀子以上。
可在層層剋扣之下,前線賣命的兵勇,拿到手的不過是零頭。
難怪鄉勇們一聽見英軍的炮聲,就如鳥獸般星散。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古老的農業社會猛然間遭遇到工業社會,冷兵器遇到熱兵器,屬實是被降維打擊了。
天朝上國,五千年曆史底蘊、廣袤國土、四億人口以及固步自封所積攢的自豪,徹底被侵略者碾壓至粉碎,化爲自卑與脆弱。
清政府官員們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敵人,茫然無措,寄希望於玄妙之事,如《道鹹宦場見聞錄》中便有以下蠱來對付英軍的故事。
再比如,官員們想象中的洋人是膝蓋不會彎曲,走路只能像殭屍一樣跳着走。因此,戰爭開始時,清軍看見洋人在陸地上健步如飛,震詫得無以復加。
最關鍵的是,開戰一年多來,朝野之中,對英國的瞭解,一如既往地匱乏。
然而,在此存亡之際,依然有數之不盡的仁人志士報效國家,以期驅趕侵略者。
閱讀貝青喬的《咄咄吟》、夏燮的《中西紀事》時,尤能感受到時人的悲憤與無奈。
《中西紀事》中記錄着戰爭中寧波、鎮海戰爭的殉難者姓名,其中便有千里迢迢從四川率領部分的土司阿木穰、瓦王寺守備喀克哩、四川營參將王國英。
可見,川軍勇猛,是有傳統的。
貝青喬記錄阿木穰之事,「阿土司所帥屯兵最勇,攻寧波時,爲頭隊,首當夷炮,與其部下四卡松等百人拼死於城內」。
揚州捕役楊泳帶着幾十名弟子,投身戰場之中。他們拳腳厲害,乃是少林弟子。
楊泳與弟子們死在巷戰之中。
鄉勇謝寶樹,在攻打鎮海招寶山時,身受重傷,回到軍營之中,傷口裂開,失血而死。
臨死之前,謝寶樹仍在追問,「猶以我軍勝敗爲問也。」
這批英雄人物,在這場力量懸殊的戰役之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這些拿着薄餉的英雄人物,與鄂雲、奕經等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南京條約》簽訂後, 除了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等少數精英在反思、在睜眼看世界之外,大部分肉食者都回到「歌照唱、舞照跳」的狀態中去。
1856 年 10 月,英法聯軍的軍艦再次攻打攻佔廣州,開啓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這一次的應對,清政府不能說沒有進步,只能說是原地踏步。
清政府再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重複着同樣的錯誤。
主要參考資料
.《天朝的崩潰》,茅海建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4
.《中西紀事》,夏燮著,中華書局,2020.10
.《鴉片戰爭》第 3 冊,中國史學會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21.9
.《清代文官選任制度》,張振國,南開大學,2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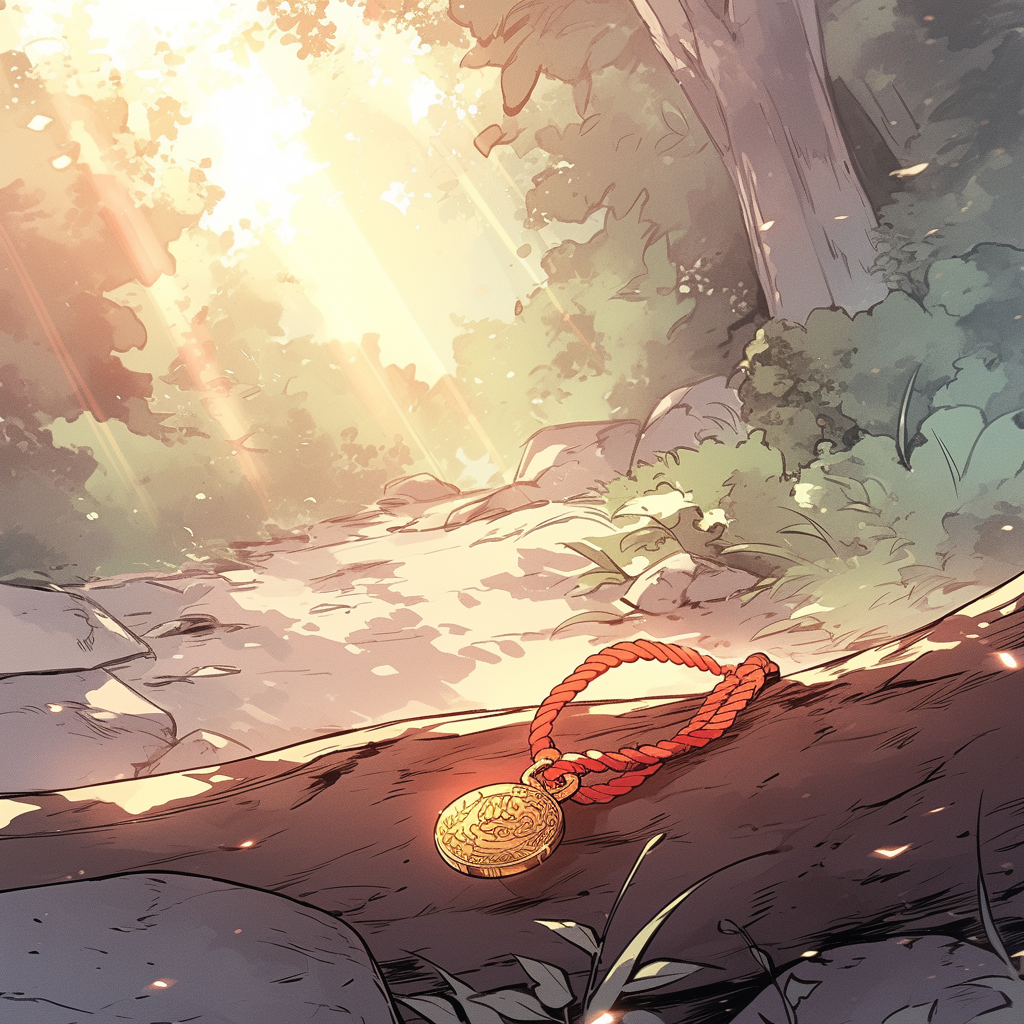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