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聲唱》完成了,我跨時兩年的小說,在秋風蕭瑟中休止鍵盤,像一臺揪心的戲劇落下帷幕。
失去父親的悲傷,仍淤積在我的心房。他是在我未完成這部小說時去世的。他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青龍崗。在他未入土為安之前,我的哀思也無處安放。他的魂靈或許已到達天堂,或許還在我身邊。怎樣都可以,總之父親在我心中是永久的存在。如今我越是看不見他,他的音容在我心目中卻愈加清晰。
小說還是要寫,就像生活還要繼續。
更何況我的這部小說,父親差點是全程的見證者。事實上初稿完成的時候,他還活著。可是我還要改,改了還要再改。父親沒有等我改完這部小說就走了。他走時像是很安詳,或許是因為他和所有的子女都見了最後一面,也或許是因為醫院給他使用了鎮定的藥。誰知道他有沒有痛苦呢?父親一生都是堅強和達觀的人,即使大半輩子都是病魔纏身,但我從沒見他喊痛。這個上嶺邨的男人,是上嶺邨最偉大的男人。
《蟬聲唱》正是獻給上嶺邨的男人的,是獻給上嶺邨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雖然故事裡沒有我的父親,甚至真實的上嶺邨的男人也沒有在故事裡。唯一真名實姓在故事裡的樊家寧,他的故事大半是虛構的。但是這部小說的後記,我必須講真實和真正的上嶺邨的男人。他們其實也是小說的一部分。不講他們,這部小說的意義達不到最大。
我要講三個男人。
第一個男人是樊家寧。他是我的本家,扯遠一點我可以叫他堂哥。我讀高一的時候,他讀高二。那年月高中是兩年制。樊家寧高中畢業不久就當兵去了。那是 1978 年 12 月,樊家寧應徵入伍,是我們上嶺邨唯獨的一個。我們菁盛鄉跟他一起入伍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叫羅夢迂,另一個我記不住姓名了。他們三個人入伍的歡送會,我去了。他們胸前的大紅花,戴在各自往日穿的衣服上。我插在敲鑼打鼓的人群中,羨慕的眼光看著他們,因為看上去他們的確很光榮。在那個年代,只有政審和身體都合格的人才能有那樣的榮光。那時候我還想,如果一年後我報名參軍,政審一定是存疑的,因為我父親和母親的原因(甚麼原因我後面會提到)。所以他們能參軍,我羨慕是有道理的。我以歡喜和凝重兩種心情送走他們,回學校繼續念書。那年的雪居然下到山下的學校裡來,被我們觸摸。而往年的雪都停留在山頂上,白白的一片,讓我們觀望而已。那時我並不覺得這是甚麼不好的兆頭,恰恰相反,我覺得來年我一定能考上一所學校,至少是技工學校。
之後不久的一天,我在家,忽然望見河對岸的公路,駛過幾輛解放牌的汽車。車上站滿了人,所有人都興奮地呼叫。後來我知道那是隔壁金釵鄉支前的民兵。
再不久,戰爭爆發了。我天天看著報紙,都是勝利的消息和英雄的事跡。我記得最深的一位英雄,他叫岩龍,是個普通的戰士,卻是神槍手。他一下子幹掉了幾十個敵人。但是有一天,他胸前掛著一副繳獲的望遠鏡,被敵人以為是指揮官,不幸中彈犧牲。我開始為我的堂哥樊家寧擔心。
過了些天,鄉裡通知學校師生去參加追悼會。在鄉政府的操場,我看到的兩張遺像,並不是我的堂哥樊家寧,而是另兩個與他一同參軍的我菁盛鄉中學的校友。他們的遺像還是穿著便服,說明他們連軍裝照還來不及拍就上了戰場。我還記得名字的羅夢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副好嗓子,他的歌喉我認為後來的劉歡、孫楠也比不上。但是他犧牲了,不到二十歲。
又過了些天,幾輛解放牌汽車又從我家河對岸的公路駛過。是支前的隔壁金釵鄉民兵回來了,他們悄無聲息,人數也比去的時候少了。我繼續擔心我的堂哥樊家寧。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堂哥樊家寧活著回來了。他只是負了傷,臀部被彈片削去了一塊,複員後被安排在鄉供銷社,當工人。他上班時我見過他一面,他在賣酒。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沒有理我。他對待其他人話也很少,非說不可才說的樣子。我估摸他還在被戰爭的硝煙籠罩著。我問他至親的人,他在戰場上都經历了甚麼?他們說他甚麼都沒告訴,只知道他在的部隊是戰地救護運輸隊,他是專門收屍的。我頓時毛骨悚然,再不敢去見他。
後來我考上了大學。大學畢業我先分回菁盛鄉中學工作。我在菁盛鄉工作的一年,只遠遠見過他一次。他踉踉蹌蹌,像是喝醉的樣子。但是我聽說他結婚了,生了孩子。
後來我調走了,十多年沒有回鄉,也沒有回上嶺邨。我每年都回上嶺邨是 2007 年以後的事情。我每次回上嶺邨,也沒有見樊家寧,因為他在另外一個屯,而且那個屯在高山的…場裡,我不上去,他不下來。我只是知道他下崗了,妻子還和他離了婚。就在 2014 年,我回上嶺過清明節的時候,才知道他不在了。他從山上下來,就在我們上嶺邨的碼頭,跳河死了。
我難受了好幾年。一直到現在,每次回上嶺過河,我就會想起他,仿佛看見他在碼頭邊的石崖上站立然後往下跳,河水迸濺出巨大的浪花,像是一顆炸彈在爆炸。他的生命和命運就終結或沉沒在那波浪滾滾的河水裡。我真想寫這個男人的生命和命運。
《蟬聲唱》寫作的初衷、動機或靈感,的確和樊家寧有關或來自他。我把他單獨構思了很久,遲遲沒有開始寫。我覺得光寫他一個人還不夠,或者說光寫人的苦難還不夠,我還得在小說中傾註足夠的溫情。
就在 2016 年,我的叔叔樊寶明去世了。我十分悲傷,他是我二十年來去世的至親的人。二十年前去世的我至親的人是我的外婆,再往前是我的爺爺。他們的去世也讓我悲傷,但過了那麼多年,我的悲傷已變成了思念。如今叔叔去世,悲傷再次襲擊了我,讓我猝不及防。
叔叔樊寶明是我要講的第二個上嶺邨的男人。
我在叔叔去世的當晚,在殯儀館,用行動電話寫了一段文字,拷貝如下:
叔叔,在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刻,在望州路 308 號——所有活著的人懼怕來的地方。安靈廳 6,我靜靜地守著您,懷念您。幾天後,我還是在這裡,送您起飛,去往沒有疾病、傾軋、貧困、欺淩的天國。您在人世遭受的疾病、傾軋、貧困、欺淩的折磨,終於擺脫給源源不斷步您後塵的人,像辛勞一輩子的牛,卸掉了沉重的軛。
您是我的恩人,叔叔。在我十五歲那年高考落榜後,在我在建築工地卸水泥搬磚五個月後,您找到了我,把我帶來南寧,在您服務的高校高考補習班補習。
在和您居住的半年裡,您比我父親嚴厲,卻比我父親更疼我。我第一次吃蘋果、雪梨,是您買給我的,雖然一周只有一個。沒有高考補習那半年,我肯定考不上大學。沒有您,我肯定是另外一種我不願意的命運。
您是我們家族的驕傲,叔叔。您不用作弊、不走後門考上大學,是我們家族第一代也是您那一代唯一的大學生。大學畢業直接留校,官至人事處長。但您大兒子至今是農民,小兒子依然下崗。他們現在正守在您身邊,無怨無悔地披麻戴孝。
您不僅是我們家族唯一的共產黨員,也是我見識的對黨最忠心的人。在您的告別會上,我希望能看到您所在的單位黨委送的花圈。
八十四歲的叔叔,您現在已經確定比您八十八歲哥哥先行來到望州路 308 號。你們兩兄弟從小失去母親,相依為命。如今您先走一步,我們還沒敢把消息告訴您哥哥——我的父親,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承受得了失去您的打擊。如果我們決定欺騙他,請您原諒,叔叔。
夜更深更靜了,望州路 308 號陰沉悶熱,我卻不感到害怕。您眾多的親人在守著你,他們大多來自上嶺,那是您出生的地方,也將是您永生的地方。「一個士兵不戰死沙場,便要回到故鄉。」您不是士兵,您是孺子牛,更要回到家鄉!上嶺青青的草地和潔淨的河流,等待您的歸去。
叔叔火化後,我們將他的骨灰接回了上嶺安葬。他的墳就在我們祖屋後面的半山腰上。從那裡往下望,可以望見祖屋、田地和田地裡親人的墳墓,還可以望見長長的河流和河流兩岸青翠的竹林。人們見了都說,那是上嶺邨最好的風水。我信。
安葬好叔叔回到南寧,我蒙在鼓裡的父親像是有兄弟間的感應,忽然問:你叔叔怎麼樣?我很驚愕,差點忍不住把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訴了他。但我最終沒有。接下來父親的舉動變得奇異——他常拿起座機的話筒然後撥號,但他是不會打電話的,怎麼都不通。我母親問他幹甚麼,他說我給寶明打電話。母親說寶明這個時間休息了,不要打擾他。後來父親要求我送他去師院看望叔叔,我又騙他說叔叔已經接回上嶺療養了,那裡信號不好,也打不了電話。叔叔去世後,叔叔的子女常來看望我父親,父親開口必問叔叔的情況,得到的答案跟我說的一樣。父親似乎相信了他的弟弟仍然健在,沉寂下來。
在叔叔去世半年後,父親的身體忽然衰弱得十分厲害。他像一臺不停使用了八十多年的機器,已經無法正常地生活。開始還能用拐杖走一走,很快拐杖也不起作用了,只能躺在牀上或坐在輪椅上。然後是部分失憶和意識糢糊,常常把看望他的這人誤認為那人。但是父親對上嶺的記憶卻非常清楚,一提起上嶺的人,許多人四十年六十年都沒再見過面,他卻還記得,並說出他們的往事。
父親臥牀不起後的 2017 年夏天,我開始寫作這部小說。對生命的無常和時間的流逝,讓我有了緊迫感。最主要的是,我的構思成熟了,就像井裡已經蓄滿了水或油,我要讓它流出來或噴出來。
在我寫作的過程中,父親的病情日益嚴重,頻頻住院。病情稍微穩定,再把他接出來,居家照顧。
在父親生命接近尾聲的時光,姐姐時常從防城港過來,悉心照顧他。我在美國的哥哥、嫂子和姪子也輪流回來看望他。我們兄姐弟自小因為分散讀書、工作,聚少離多,因為照顧和看望父親,這居然是我們共同在一起時間最長、較親密的日子。有哥姐的照顧和關懷,使我的寫作得以斷斷續續地進行。
接著我該講上嶺邨的第三個男人了。實際上我已經在講了,他就是我的父親樊寶宗。
關於我的父親,這個給我生命和這個人世間最愛我我也最愛的男人,在 1996 年,我曾經寫過一篇以他的姓名命題的文章,拷貝如下:
樊寶宗
現在,我請求尊敬的編輯,不要刪改文章的題目,因為這是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的。我的父親今年七十歲,他桃李芬芳,但他的名字卻從來沒上過報紙。他不像他的兒子,年紀不及父親的一半,就有了許多的虛榮。這些年來,我寫過許多的人物,但父親的名字卻從未出現在我的任何文章裡。如今回頭一想,我真是很傻。我的父親當了一輩子的教師,教過的學生成千上萬,而他的名聲卻遠遠小過他的學生、他的兒子,更小過他的奉獻和價值。對比我寫過的諸多人物,我其實早應該或最應該以父親為題寫一篇文章,為父親揚名,盡管我的父親早已越過功名利祿的欲望和年齡。
父親的一生厚重、高尚,如他教過的書,又普通渺小如一支粉筆,或如他兒子的名字。
就像我是父親的親生骨肉一樣,我的名字是父親所賜。我先後有過兩個名字。樊益平——這是我父親為我起的第一個名字,它像一份零亂蕪雜的自留地,為我耕用,直到我中學畢業。
1980 年的那場高考,是父親為我填報的志願。在填寫志願之前,他首先修改我的名字。凡一平——父親在為兒子修改名字的時候,是多有勇氣啊!他居然敢於把祖宗的「樊」姓給革了。而在這之前,他已把我哥哥的名字改為凡平。從「樊」到「凡」,父親用心深長,而寓意、願望又顯而易見。而河池師範專科學校,我父親的選擇,成為我至今感念不忘的母校。那年,我十六歲,我還理解不了父親,然而我的血液決定我無法像很多人一樣鄙視教師的職業。我進了這所學校,是這所學校煥發了我的真情。我從未如此強烈地感受著教師的榮辱在我心靈的回旋噴薄。
我正式用父親親手為我修改的新名開始發表作品。我記得當我把在《詩刊》發表的處女作《一個小學教師之死》寄給父親時,我附信中說:爸爸,我正在理解你為甚麼叫我作凡一平。
從此「凡一平」一直被我使用著,它像一盞普通的燈放出的光,為我照明。這些年以來,不知有多少人煽動我,把名字給改了,改換一個稀奇古怪的名字,沒準能在文壇出大名,我說,我不改,因為我的名字是我父親給我的。
此刻,我寫這篇短文的時候,父親就在我的身邊。但是他看不見我寫的東西,因為他弱視嚴重得幾近失明——父親弱視到無法批改學生的作業才離開山邨小學的。他告別煤油燈和手電筒,被我接來南寧居住。然而不論城市的燈火如何燦爛,都不會使父親的眼睛感到刺激或受到影嚮。他看不清書和電視。時常有親友來訪,他屢屢將我誤看成他人,與我握手。現在,就算我把他的名字寫得再大,他也看不見。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敢將父親的名字登報。
1996 年
以後的 2009 年,我又寫了一首關於父親的詩,準確地說,是關於我家族的一組詩,整組詩是這樣寫的:
家族(組詩)
我家族的每一個人
都是一首詩
如果不是詩
就是我的春天
—— 題記
樊光燿
我沒見過哪個男人能像我的祖父
沒有女人也可以活得下去
他是紅水河上的船夫 美男子
不信你們看看我的父親和叔父
他們年輕時候的照片
帥得我不認識
1928—1932 年間
兩顆星星呱呱墜地
把承載他們的草屋
照燿得一窮二白
然後祖母扔下她和祖父共同創造的作品
去了天堂
三十二歲的祖父
直到八十一歲去世的那天
沒有一絲緋聞
多麼可憐的男人
打著光棍
撫養兩個小男人
不讓他們上山砍柴 下河打魚
卻送他們上學讀書
這在七十年前的上嶺邨
蠢得出奇 絕無僅有
連祖父也不知道
他在當年就擁有了兩只股票
每年都在漲 漲到如今
已經非常非常寶貴了
祖父同樣不知道
他用來卷煙剩下的半本書
傳到我這個孫子的手上
像一雙翅膀 或千裡眼
我在想象的世界裡飛翔
放眼人生
得益於這本書的開發和啓蒙
那是半本《紅岩》
祖父 你臨死的前一天晚上
如果不誤把煤油當酒喝了一瓶
就不會死
就會繼續把那半本《紅岩》當卷煙紙
撕到最後一頁 那麼
你的孫子就得不到你的遺產了
祖父又一次做了蠢事
上次是為兒子
然後為孫子
樊寶宗
一個陌生的男人
在我十四歲的時候見到我
他在大庭廣眾下驚呼
「長得很像樊寶宗,你是不是樊寶宗的兒子?」
我憤怒地撿起了一塊石頭 因為
他竟敢直呼我爸爸的名字
我心目中的父親就像聖上
他的名字,兒子不能叫
我以為別人也不能叫
父親是上嶺小學的一名老師
他用粉筆寫聖旨
也用紅筆批奏折
他受人尊敬、擁戴 只不過
他的領土就上嶺小學那麼點大
他在那裡當王 當到
雙目幾近失明 不能再當
身患疾病的父親所吃過的藥
有一噸還多
把一個家壓扁了
但是沒有垮
因為有一個女人撐著
那是我的母親
從 1996 年開始 奇跡
像鐵樹開花
父親不再是醫院裡的常客
現年八十一歲的父親
樂呵呵地生活著
每天爬一次到兩次七層樓
最關心天氣預報
最擔心的是我的肥胖
對我生病的母親俯首帖耳
反過來悉心照顧她
他們的婚姻已經鍍上了金子
讓許多人難以望其項背
潘麗琨
我發現我身上的基因
母親的要多一些
這個進入樊氏家族的女人
渾身是藝術的細胞
我確定這一點的時候
母親已近八十歲了
她開始寫小說、散文
使用我淘汰的 IBM 電腦
每天可以敲三千字
至今已發表中篇小說一部
短篇若幹
因為年近八十而被作家東西譽為
80 後作家
她文筆優美 描寫生動
以至於東西懷疑我所有的作品
出自母親之手
母親特別珍惜她所得的稿費
因為她窮了一輩子
有一次我和朋友打牌輸了
母親的稿費在我的口袋裡蠢蠢欲動
過後母親語重心長 說
兒啊,別打那麼多牌了,我怕我寫不及呀
這故事是東西編的 但的確是
母親的心願
通過母親的作品 我才揭開
母親和父親結合的祕密
她是地主的女兒
唯一享受的好處是讀書讀到中專
那是在解放前
解放後的母親
像在石頭縫中求存的草
母親這根草
嫁接到僱農的父親家裡
得到保護
母親在樊家 沒有享福
她像丫鬟一樣為樊家服務
伺候我長年患病的父親
撫育姓樊的兒女
母親寫得一手好字的手
腐蝕在水深火熱的年代裡
但是母親愛丈夫
更愛她的兒女
她的愛靜寂深遠
像一條大河
2009 年 11 月 3 日
這組詩裡的「樊光燿」是我爺爺,「潘麗琨」是我的母親。說到我的母親,她和我父親的結合,在詩裡已有表述。因為母親的成分高,當年嫁給父親是最好的選擇。也因為父親娶了個成分高的妻子,在他正值大好前程的年紀,一直不被重用,甚至被批鬥。1969 年,父親母親被下放回到上嶺邨,在上嶺小學當著拿生產隊工分的教師。因為母親成分的關系,我們哥姐弟在上學期間的待遇也有別於他人。1977 年,我哥哥考上武漢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到了鄉裡,還被鄉黨委書記扣押,差點誤了升學的機會。我在中學時強烈申請加入紅衞兵都不被批準,乃至我讀大學時也是班裡唯一沒有獲準加入共青團的人。或許因為歉疚,母親對她的兒女和丈夫照顧得特別好,尤其體現在照顧從三十歲就開始患慢性病的丈夫上。
我現在清楚記得小時候父親每每被送往醫院的情景。他被人從另一教學點抬下山來,常常是在深夜,那時我從睡夢中驚醒,父親哮喘的聲音灌滿家門。這時候母親便去找擺渡的船工。父親需要渡河,才能被送往公社的醫院。船工終於被母親請來,父親被抬到河邊,上了船。悽涼的夜晚,風吹水緊,我站在漆黑的岸邊,望著明明滅滅的星零船火,諦聽飄搖的槳聲,將我父親送到對岸……
父親被母親照顧了整整六十年,直到他今年九十歲去世。
2018 年 11 月 1 日 10 時 29 分,這註定是我們全家悲傷的時刻。在醫院 ICU 在醫病牀上,父親停止了呼吸。在他停止呼吸之前的半小時,我們兄姐弟集中在牀邊,告訴父親他的弟弟、我們的叔叔已經先他兩年去世的消息。父親一定是聽見了,他的喉結狠狠地蠕動了一下,又蠕動了一下。那時刻我的眼淚嘩嘩直流,正如我此刻寫這段文字的時候。父親,對不起!
在父親去世的那張牀上,我們哥姐弟為父親擦身、穿上衣裳、鞋襪,為他蓋上壽被。父親幹幹淨淨地走了,正如他幹幹淨淨地在人間。
父親重病的晚期,已氣弱不能大聲說話。為了晚間他需要方便的時候人能聽見,我們給他一個鈴鐺,拴在他的手上。父親不斷地搖著鈴鐺,有時候真的是為了方便。更多時候是想搖就搖,我在寫作的時候聽到鈴聲過去,甚麼事都沒有,弄得我有些不耐煩。我現在知道,父親是希望有人陪著他。可現在知道已經晚了。我再也聽不到父親搖曳的鈴鐺聲,再也不能陪父親了。
父親被送往殯儀館。我們在殯儀館設了靈堂。父親去世的消息傳到上嶺,上嶺邨的人們紛紛或從上嶺或從異地前來吊唁,並與我們親屬一同守靈。在守靈的兩天兩夜,我看到上嶺邨人對父親的尊重和敬愛,這讓我沒有料到。父親離開上嶺邨二十八年,再也沒有回去過。可居然還有那麼多人沒忘記他,懷念他。更讓我沒有料到的是告別會上,一下子又湧來了二百多人。他們是父親的學生們,最小的起碼都四十多歲了。當然還有我的朋友們,他們與其說是來慰問我,不如說是來悼念一個值得尊敬的小學教師。
父親火化前後,我們殷勤甚至拼命地為他燒紙錢、燒別墅、麻將、撲克牌,因為這是他生前最缺的東西,所以我們希望他死後擁有。父親一輩子的收入,都花在了治病上,交給了醫院。父親這下好了,燒給他的錢足夠花了,隨便花,因為天堂沒有病痛,也就沒有醫院。
還有,父親生前最愛戴的一塊手表,是我在北歐給他買的,他非常喜歡,即使眼睛看不見也要戴著。父親心跳停止了,這塊表還在走。當手表放進骨灰盒的時候,表還是在走。
父親去世的時間比金庸晚了一天。他追趕金庸並不晚,一定能趕上。盡管他不認識金庸,金庸也不認得他。但願父親在天堂能加入金庸的江湖,因為父親一生俠義、仁厚、忠良,金庸一定會收留他。
父親和叔叔,這兩兄弟,終於在天堂相會,繼續做兄弟了。
幾天前,我畫了一幅畫,畫的是兩只仙鶴,在山巒上空飛向天堂。那是上嶺的山巒。父親和叔叔兩兄弟曾在那裡相依為命,如今也從那裡如鶴杳去。
…
上嶺邨三個男人的故事講完了,他們是《蟬聲唱》後記最主要的內容,是這部小說的補充和解釋。對我來說,其實有這篇後記就夠了,因為有我父親、叔叔、樊家寧這樣上嶺邨的男人,才有《蟬聲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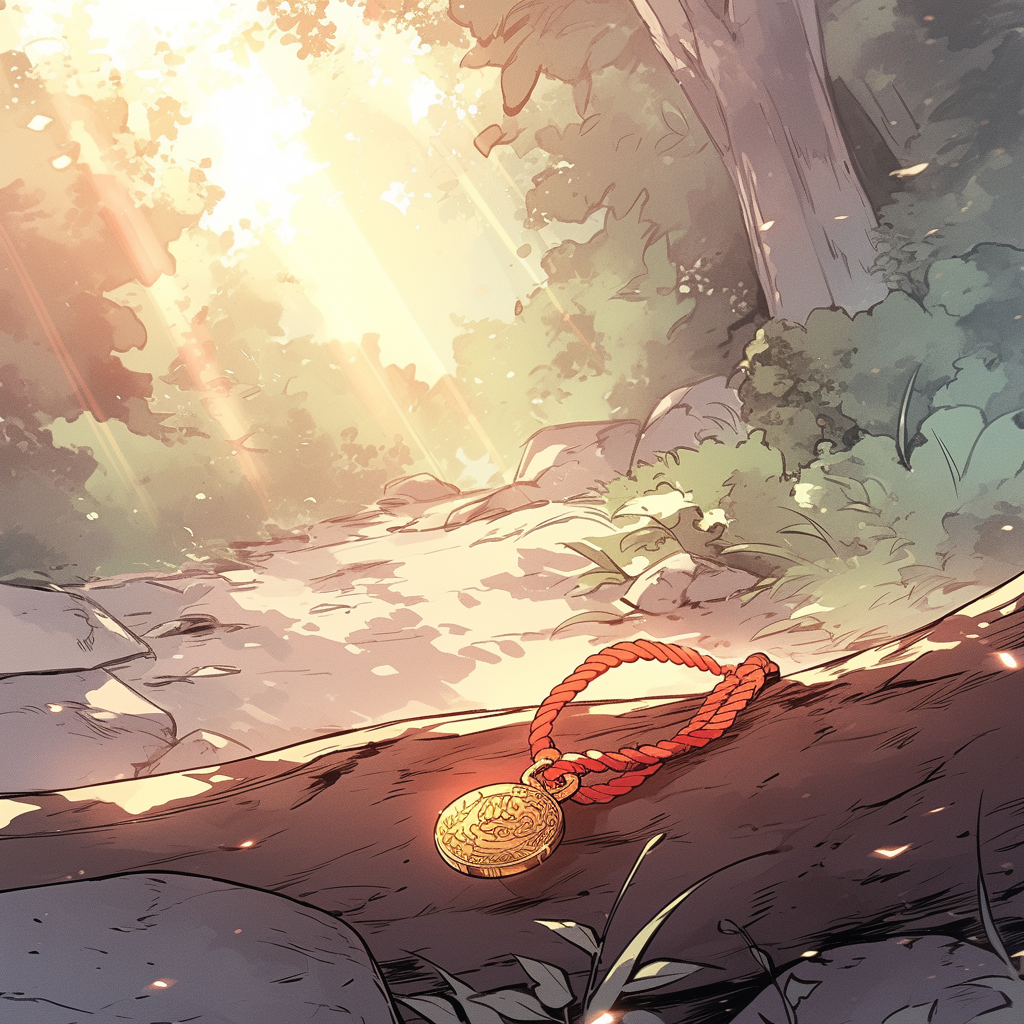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